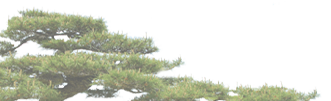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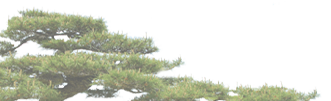

于崇良 ,山西省定襄縣人,曾任忻州地委委員。地委秘書長。
1991年夏季的一天,省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武正國同志通知,華國鋒及其夫人一行次日上臺山,要我陪同一齊去。我把通知轉告張秉法書記和金銀煥、范堆相兩位副書記,他們提出路經忻州,能不能接見一下地委領導。我請示正國同志后,很快得到答復,可以接見,但范圍一定要小。于是第二天上午八點半,地委幾位主要領導就到賓館103房間(貴賓休息室)等候。不久,在警車的引領下,由正國同志陪同華國鋒、夫人、秘書和醫護人員、警衛等六七人進入賓館,我們在北樓門廳外迎接客人進入房間,依次就坐,互致問候,稍事休息,在樓前集體照了像,簡單的接見就這樣結束了。
『沿途的活動』 出發時,我正準備上自己的車,正國同志喊我同他一起上了中巴(主車),以便回答華國鋒有關忻州的問題。因為事先沒有思想準備,開始還有點緊張,怕答非所問,尷尬難堪。可上車以后華國鋒像對待一個晚輩一樣,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很快使我忘掉自己是在同一個曾經擔負黨和國家重任的人物交談。一路上華國鋒問長問短,話題很廣,有農村形勢和農民生活的內容,有改革開放的內容,偶然也談到當時國際上的一些熱點問題。交談中,我大膽表明了對我們黨幾十年來,每當出臺一項全局性政策時,總是犯一刀切的錨誤。其根源是中間環節的領導積極保護自己,消極對待中央的思想作怪,不是把中央的政策同本地的實際結合起來,而是上邊咋說他咋做,出了問題免他負責。就說這次在農村推行的土地承包吧,一些集體經濟雄厚的地方,群眾并不想散伙,為什么不能留一些先進村隊等一等,看一看,根據群眾意見決定去留呢!華國鋒的微笑和點頭,使我更加大膽的說,土改時我們曾把土地平均分配給個人,可有的是越種越好,連續增產,有的是越種越荒,不斷減產,接著土地就自然地向種田能手集中,我們還把人家當新富農批判打擊。這次按人頭承包土地的方法,實際上在一些農戶也隱藏著一些影響發展生產的影子。以后肯定還會通過轉包、租賃等形式,向種田能手集中,但愿以后不要再以新富農的罪名打擊種田能手了。
不知不覺,車已進入定襄境內,華國鋒看到忻定盆地這塊肥沃的土地上茁壯的禾苗,顯的特別高興,說“現在農民種地的積極性比過去吃大鍋飯時高的多了”。路過蔣村時,順便看了薄老的故居,接著又在河邊和五臺的永安分別看了閻錫山和徐帥的故居。從永安出來,華國鋒問大家看了以后的感想,大伙七嘴八舌,紛紛議論,“閻府的一磚一瓷都含有山西人民的血汗”,“薄老和徐帥的故居都證明他們是農民的兒子”,“兩頭簡陋,中間豪華,代表了不同的階級,不同的出身”。華國鋒高興地肯定了大家的看法說:“這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區別,也是他們失敗,我們勝利的原因。”由此使我想到一些老同志看了閻錫山故居后激憤地說,“兩邊的薄徐故居那么普通簡單,中間的閻故居那么氣派,這是在長敵之威,滅我之志”。因此提出把閻故居改為什么什么館,這些老同志忘卻了起碼的常識,故居是文物,而文物是歷史的見證,把某一故居改名為別的什么館,都是在抹殺歷史的本來面貌。對同樣的事物產生的兩種不同的看法,反映出兩種不同的思想認識和思維方法。一種是形而上學的形左實右,一種是唯物辯證的階級分析。在真實歷史基礎上的階級分析,揭示了我們黨同國民黨不同的階級基礎和政治性質。由此看出,華國鋒與一般老革命相比,思想認識水平顯然不是同一層次。
中午趕到五臺縣城,在賓館就餐。不知是因為有警車開道,城里人感覺到有大人物來,還是縣里把華國鋒來的消息傳出去,午飯后一出餐廳,賓館反鎖的大門外已經重重疊疊,人潮涌動,有呼喊的,有鼓掌的,有使勁招手的,所有的人都把自己的熱情毫無保留地傾瀉給華國鋒。華國鋒快步走向大門,向大家招手說:“鄉親們好!”并把手伸出大門鐵欄,盡可能夠著同大家握手。最后才勸說:“大家回去吧。”不知是群眾的熱情像暴雨般很快瀉盡,還是華國鋒的勸說起了作用,在華國鋒緩緩退后的瞬間,群眾也依依不舍地有序散去。
午睡起來,告別縣領導之后,車隊啟程,經豆村向臺懷駛去。到了金閣寺,按計劃下車參觀,華國鋒健步走在通向寺門的石階大坡上,我們分左右及隨后而行,以便保護。寺內短暫參觀后,一出門就有許多游客和就近的群眾,或圍在門口搶先目睹,或分左右靠近陡坡兩側護墻,目視歡送。一個將近六十歲的老農,以神奇而興奮的目光一直注視著華國鋒,忽而緊走幾步迅速向坡下移動,忽然又急速停下,回頭再看,如此反復幾次,突然大聲喊出三個字———“華主席”。華國鋒微笑地握住老農的手親切地問候幾句就說,“我是華國鋒”,一是證實自己的身份,二是糾正老農不妥的稱呼。走下臺階以后,又問路邊擺攤設點的小商販,家住哪里,離這多遠,家庭人口和收入,路邊攤點的效益等,使我深切地感覺到他雖然身不在要位,卻仍然心系著群眾。
因時間緊迫,在工作人員的催促下,大家又各上各車向臺懷進發。
『臺懷小住』 在太陽快要落山的時候,到達臺懷,下榻省政府的接待單位———棲賢閣賓館。
第二天早餐以后,在臺懷的景點集中區游覽。來到顯通寺的藏經樓院內,主持早就在休息室等候,進屋就坐品茶寒暄之后,就上藏經樓參觀珍貴文物,下來就上鐘樓,還試著撞鐘。隨著時間的推移,游客也相應多起來。所以從銅塔銅殿走下來以后,許多游客,特別是以家庭或親友為單元的,都爭相交替靠近華國鋒,邊走邊按快門,以留下這難得的瞬間。其中一對中年夫婦反復把自己的小女孩推近華國鋒拍照,在省廳警員多次勸阻無效的情況下,警察強行把相機沒收準備曝光,華國鋒不悅地說:“和我們一齊照個相,有什么不可以,人家大老遠來一趟,很不容易,一個膠卷照了幾十張,就因為同我們照了幾張就曝光,太過分了。”聽到華國鋒的抱怨,我立即退后幾步,靠近警衛,耳語轉達了華國鋒意見,并示意把相機還給人家。中年夫婦接到相機,客套了幾句就很快離開。一場警員與游客的小磨擦就這樣結束了。
隨著中午的臨近,人潮也越來越盛。那時候,人們對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或曾經是國家領導的人,都有一種好奇和神秘感,這就給警員和隨行工作人員增加了很大的壓力。從菩薩頂下來的時候,本來坡陡路窄,加上人多擁擠,當時最緊張的莫過于警衛人員了。我緊隨華國鋒背后,用肩背使勁扛著人潮,以防把華國鋒擠倒。緊張而艱難地走下來之后,才發現自己腰酸背痛,不過心里卻松了一口氣,總算安全地下來了。在毛主席路居館,因為游人很少,華國鋒看得很細,問得也很具體。參觀結束回到休息室,早已擺好文房四寶,在當地領導的請求下,華國鋒欣然命筆,寫了“清涼圣境"四個大字。一上午的緊張活動就要結束時,在導游的提意下,大家在五爺廟前邊的空地里,以白塔和菩薩頂為背景,同華國鋒集體照了全景像。
因為上午的勞累,中午休息時間比較長,下午大家就近看了南山寺。與上午相比,輕松很多。晚飯以后,出來散步,外地游客都入住休息,棲賢閣大門外也特別安靜。在小溪邊,在石橋上,在小樹林里,轉來轉去,有說有笑,悠閑自在,輕松愉快。華國鋒的夫人深有感觸地說:“難得如此消閑。他在位時,連春節都不能回家同我們一齊過,更別說其它節日了。老華愛吃糕,都不能隨意由自己吃,那能像現在這樣輕松自在。"
第二天,驅車到臺懷較遠的重點景區,有選擇的參觀。首先上了南臺頂。站立臺頂極目遠眺,方知天外有天,宇宙之大,而腳下卻是一片花海,頓覺進入仙境,很是心曠神怡。此時,導游指著其它四個臺頂的方位,掌心向上,豎起五指比劃,每個指尖代表一個臺頂,景點集中的地方正好在五指下方的掌心處,由五個臺頂環抱,所以叫臺懷。這一天行程雖遠,路也跑的多,但因為遠離鬧區,游客很少,是警員和隨行人員最輕松的一天。可誰都沒想到,在我們輕松游覽的時候,我國北方那個大國卻發生了最為震驚的,足以改變世界局勢的大事件,氣氛顯得特緊張。
晚上返回棲賢閣,大家正在議論一個爆炸性的新聞———蘇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會議表決,把戈爾巴喬夫趕下臺,由正統的共產黨人掌了權。聽到這個消息以后,我們同華國鋒的隨行工作人員都很高興,特別是比較年輕的同志,更是興高采烈,拍手稱快。但是華國鋒卻很平靜的說:“現在鼓掌,為時尚早,戈爾巴喬夫決不是單純的一個人,今后的斗爭會更復雜,結果如何,很難預料。”事后蘇聯的解體證明華國鋒不愧是戰爭年代走過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具有領袖人物的思維和遠見。
『尾聲』 華國鋒在五臺山活動結束的時候,秘書問我有什么要求,我便斗膽提出,能否讓首長留點墨寶給我。秘書肯定地回答,一定轉告。返回太原之后,華國鋒為我寫了“勤奮”兩個大字,右上幅的小字是于崇良同志留念,左下是華國鋒的落款和時間。
1992年夏天,我的前妻因食道癌在北京手術治療,我陪同住在三晉賓館。一天,中學的同學郭武魁(五臺人,外語學院畢業后在京外事部門工作)攜夫人同來看我,并以其夫人癌癥術后多年一直很好為例,給我老伴解心寬。閑談中他突然問我:“你來京這么長時問,看過華國鋒嗎?”我說:“我憑什么去看人家。”“你不是陪他上過五臺山嗎?”“你怎么知道?”“因為他夫人是我們五臺老鄉,每年春節,我們幾個老鄉都要去。華國鋒說起你來印象很深,說你腦子好,看問題深刻。你應該去看看。”按照老同學的意見和他留下的聯系電話,我委托譚周君同志事先聯系好,第二天上午我和譚周君等遵照約定按時去。第一道門的警衛問清我們的身份后說:“首長有通知,進去吧。”第二道門是華國鋒的院門,也有站崗的。老遠我就看見華國鋒的夫人已經在門口等我們了。我們緊走幾步趕過去,老人熱情地和我們打招呼,并向警衛示意以后,一直把我們引進院內,一看就像過去王爺們住過的古老宅院。正面中間是客廳,進入客廳,老夫人說老華正在用餐,請稍等。我們還沒有坐穩,華國鋒就走進客廳,我們馬上起立,華國鋒很快招手示意說,坐下,都坐下。看見華國鋒,我目測的感覺是比前一年瘦了點,但精神仍然很好。他像一位慈祥的長者,與我們交談。對山西和忻州的變化很感興趣。我們都把他感興趣的問題如實作了回答。聽說華國鋒患有糖尿病,我們怕影響他的休息,不多一會兒,就主動告辭了。華國鋒的夫人把我們送出門外,我們已經走的很遠了,回頭再看,老夫人還向我們招手,像親人離別一樣,難分難舍。
(該文摘自《五臺山》雜志2008年第5期)